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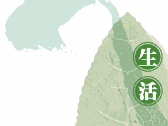
海上旧梦归何处 ○郝建
一、情怀何处
暗褐油黄色调的木制旧阁楼成为对面窗口的风景;萨克斯悠缓的
音调弥漫在酒吧中;蜡烛光在柔光镜拍出的朦胧光影中诱人地摇曳着;
夜晚,闪烁的霓虹灯光下,女人的旗袍和高跟鞋之间若隐若现的玉腿
吸引着那些唯美或淫邪的目光;昏暗的房间里,大烟枪中喷出的白色
烟雾回旋在颓废男女的脸上。他们的眼睛微微眯缝着,同睡在一张卧
榻之上。他们也许是商战中的对手,也许是老板与被喂养的金丝雀,
也许是拆白党钩住了有钱的少妇。伴随着这些画面的,是巩俐(她由
黄土地走到了上海滩)和王菲(她从北京去香港唱红)那对着老式麦
克风唱出的二、三十年代酒吧小调或舞厅浪歌。
一个令各种人无限遐想的旧上海在这两三年内从银幕上浮现出来。
她令多少人沉思、迷恋,她又令多少人恶心、愤怒。
这里并没有一个“上海题材”,这是“旧上海题材”或“怀旧题
材”。电视剧《孽债》和电影《上海假期》一类的作品虽也取材于上
海生活,但在艺术趣味、观念内涵、甚至接受群体等方面和这些作品
都大异其趣。我所关注的“旧上海题材”影视作品有其核心风格和较
集中的特征。一个旧日的上海其实是我们今天的想象的现实,更有可
能的是,她里面藏着些我们对明日的幻想。这个海上新梦通过一批作
品浮动、凸现出来,它穿过层层烟雾向我们飘来:陈逸飞的《海上旧
梦》和《人约黄昏》、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
《风月》、香港最新版的《夜半歌声》、侯孝贤的《海上花》。
女作家关于上海的风花雪月、金枝玉叶的文字也吸引了出版商和
读者的浓厚兴趣。于是,我们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式的呼啸、吼
叫和北京的皇城根下调侃的笑声中又找到一份亦新亦旧的矛盾情怀和
可圈可点的文化景观。就象陈逸飞《海上旧梦》中的迷人女子一样,
旧上海一直在向我们频频回首、顾盼含情。那个旧上海通过一九七三
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问上海时国内白发老人激动的泪水表现出
来;通过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街头一下子冒出的西服表现出来——那些
西服虽然料子笔挺做工考究可式样却极老旧。那个旧上海影响了我们
的(智慧结构、民族心智和商业交往契约,她也通过今天许多科技、
工商要津上的吴侬口音反映出来表达不明晰简洁)。
好像是突然间到了梦醒时分,艺术家们奔向那风格陈旧的石库门,
倘佯于不很光彩的四马路,聚焦于高跟鞋、石子路面、烟雾蒙蒙的雨
巷;他们从大马路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上挤下来,又坐进了二马路上
车夫拉着吃力快跑的黄包车。心血来潮时,艺术家还会让穿旗袍的女
人拉黄包车。
这是怀旧还是前瞻?这仅仅是个人迷恋,还是百姓喜欢的趣味?
(这是少数艺术家跟在现大洋叮铛声后面的昏昧迷走还是大众心底跳
动的整齐节拍?重复而学生腔)我喜欢看这些电影。这时,我得听小
金宝/巩俐一句话:你要看就看个清。
二、怀旧的意味
当北京怀旧怀到《红太阳》歌带的鼓噪和文革的歌声中去时,当
湖南的怀旧落实到每天在毛泽东塑像的基座前响落二寸厚的鞭炮纸时,
当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将愚昧的封建造神和可怕的政治怀旧搅在一起,
纷纷在车头挂起伟人像避邪时,上海点燃了另一种怀旧,画出了另一
个中国。
这里头有些意思。为什么在今天老老少少会不约而同地情怀旧上
海,为什么观众也跟着他们一起凝视那个声名暧昧的旧上海。陈凯歌
对上海感兴趣 可能是认识到旧上海虽然人欲横流血泪斑斑但又有
“非常高的层次”,这又为“今天的中国发展提供很多经验”。
陈逸飞则声称《人约黄昏》这样一个三十年代的凄美爱情故事与
他的“美学观和艺术观比较吻合”。
为什么只是在今天,旧上海那柔和斑驳的黄调子画面才重新迷人
起来。这都是商业社会闹的。旧上海绝不仅仅关乎于旧上海,老百姓
高屋建瓴一针见血眼明心亮地指出:这是新中国在怀念旧上海。前两
年我们都忙着到黄土高原、湘西世界去寻根或与各种政治话语吵架去
了。只有在向商业社会迅跑的今天,“先前富过”的上海才成为一种
难得的参照。这是我们对商业文明追求和拒斥的矛盾情怀。(这是商
业规范、社会伦理和审美话语的接轨,而不是八旗子弟守着铁杆庄稼
没事偷着乐的那份自得、安稳和高贵。这是敢漂洋过海、敢当小学徒、
敢开豆腐店的老板梦,不是提笼架鸟的公子哥们午后的那份儿惰性和
悠闲自得。这里的意味就是集体的迷恋。这些意识的湍流和美学的碎
片其实是我们中国大陆百姓的集体无意识在摸着石头过河。文风浮躁)
这里面显着一种得意,这是中华文化抖起另一面威风的得意。只是这
次抖起的不是一块红布而是铺天盖地的黄绸子,那是一块用来包钱的
黄绸子。
三、怀旧的趣味
同是怀旧,又因为笔触和用墨不同而显出不同的色调。有的黄色
泛出些古铜色而更象商业性的“行画”,有的在黄里泛出些苍白,有
的则因为溅上了血迹而有了几分惨烈。
这一轮怀旧梦由陈逸飞发动不是偶然的。他早年画过巡回展览派
风格的主旋律作品《攻占总统府》。旅美后,他的画儿卖得了好价钱,
为了卖更多的画才为自己拍了个大广告《海上旧梦》。那非叙事的
松散心理结构看似现代,可在今天其实是古典。那部片子的现代性在
它的视觉风格上。影片中最富于现代趣味的是那段用高速拍就的穿
旗袍美女拉黄包车的奇谲意像。对我而言,这一段意像的营造能力
和才气超出他整个的《海上旧梦》和《人约黄昏》。其中的矛盾意味
和对旧画、旧电影的相关使用令人着迷。这一段是根据画来的画中
之画,根据电影来的电影之电影。
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则用对经典强盗片类型的掌握
来表示他那一以贯之的平民趣味,其中很多元素使用得颇有力度、颇
为精巧。可他不肯象科波拉拍《教父》那样把经典类型的技巧用到华
美、精致来赢得票房和名声。他的这部作品把许多元素做了双元对置:
规矩的认同、反叛;平和、安祥的世外艺术活法与上海的匪盗竞争世
界。这让许多评论家失去了平衡。在那个荒岛上,他的镜头从落日中
的粼粼经过云中的太阳一直摇到天上。太阳、地平线这种在第五代导
演手里处理极慎重、极有意义的符号到了这里却变得毫无美感和语焉
不详。张艺谋的镜头为什么这样东张西望,而这部影片的票房成果说
明它与百姓是趣味相投的。这是我们民族今天的人格分裂,一边想在
国际上加入商业游戏、进入有规则的政治对话;一边又一步三叹,留
恋那童谣心境和荒岛上芦花摇荡的清清世界。结尾处,小姑娘不知道
妈妈到那里去了,却只关心到了上海“有没有新衣裳穿”、“有没有
漂亮东西戴”。水生那几个可能帮他圆豆腐店老板梦的银元叮叮铛铛
地落到江水里去了。一个孩子眼中倒置的世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那
个又令人恐惧又不得其门而入的商业社会,这是我们追寻不到的梦中
上海。
陈凯歌的《风月》则有他的一贯签名笔法:较为激烈的戏剧性和
较极端较有力度的情感迸发和个性活动。看他这几年的片子,我分不
清他是为了商业化进行极端描写还是对人性深刻的认识和挖掘。
他是为今日中国拍这片子。他认为“三十年代的上海基本已经是
一个秩序的社会。游戏的规则已经基本形成。而二十年代的上海,规
则不明确,让我联想到我们所生活的今天”。(引自台湾《影响》
95年5 期 总61期75页)
四、重回主流与重写大众
一时间,这个旧上海的新画卷竟有蔚然成风、汇聚成潮之势。
可很多人忘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作品都具备三、四十年代被斥为
“逆流”、“文娼”的通俗作品的典型风格。那就是大名顶顶也臭名
昭著的“鸳鸯蝴蝶派”一类的通俗文化。(我喜欢这种文风,其实更
有力度,更势不可当)当时的主流是新文学中的左翼革命文化。今天,
打出来的媳妇熬成了婆,当年的边缘艺术今日成了主流。那时,茅盾
曾臭骂这类作品是“真艺术的仇敌”,“对于艺术的不忠诚,再没
有比这厉害些的了。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
是可以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
(引自《蝶魂花影惜分飞》 载《读书》1993年9 期)
著名左翼影评家王尘无更从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批判美
国商业电影:“利用着醇酒、妇人、唱歌、跳舞之类来麻醉大众的
意识,……
使大众们忘了时代、忘了社会,忘了阶级……在麻醉中沦亡、驯
良地匍伏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之下。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潮中,我看到
一种强调自我升华的政治感和高扬革命、解放神圣旗帜的精英文化姿
态。它与基于个人主义和商业伦理的市民文化形成抵触和竞争,二者
几乎不能互溶和宽容。有趣之处在于,现代城市平民生活既产生了枯
寂的人生感受和马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又产生了更为丰富、刺激、自
由的平民艺术和都市文化,也有了普通小民的活法。
这样,经过了约半个世纪,当年也曾自认为是主流而在一片骂声
中硬撑的张恨水、范烟桥们终于发现市民艺术又成了主流。这一回,
却有国际级的导演扛鼎,有摞到天花板的银元支撑(没有人这么摞,
此比喻缺乏表现力)。
陈凯歌、陈逸飞的三部作品都有很典型的“鸳鸯蝴蝶派”特征。
有的是直接改编自当年的这一流派文学作品,有的具备了这一流
派的几乎所有要素;有的从片名就能读出其风格,陈凯歌的电影《风
月》原名是《花影》,而《读书》杂志上唐小兵有篇为鸳鸯蝴蝶派翻
案的文章就名之为《蝶魂花影惜分飞》。这些作品在题材上也让人遥
想当年:小处的人生、多角恋爱为主、偏爱强化至变态的个性描绘。
在深层思想上,今天的作品也与当年一脉相承:不再吹响集体的、时
代的号角,不再种情于历史大浪上的激扬人生而是描写那多种色彩的、
有时眩目到刺眼的个性图景。仅就《风月》而言,我就看到从当年的
鸳鸯蝴蝶派到张爱玲到王安忆那思想和趣味的一脉相承。那个往孩子
脸上喷大烟的镜头不就是张爱玲的记忆?
这里比较费神的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部作品与“鸳鸯
蝴蝶派”无关。那张艺谋今天扛的什么鼎,弄的什么潮?
其实,他还是主流。这是他第一部彻底学习美国强盗片叙事模式
的作品。这是世界范围内主流商业电影的经典形态:类型电影的王国。
这是外国的市民艺术,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可是,正如
前面所说,张艺谋没象科波拉那样精益求精地使用既成的形式系统,
而加入了更多的艺术态度。然而,在转向大众、不避通俗这一点上,
张艺谋又得了风气、领了风潮。这决定了我把他归于新上海梦营造
者的先锋队伍。承认大众选择,在通俗艺术的活动中建立商业伦理,
这是今日的先锋。不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或歌颂党的活动,这是今天的
一大发明。
五、谁找寻谁(这层意思似应另写一篇,现在搅在一锅不好)
面对这些新画面,我们又听到一些老调子;一个近年来进口、而
且被我们反复弹唱的老神话:你们又在为西方训服“他者”、定位
“他者”,你们又在迷恋殖民地文化。有的爱唱后现代、后殖民调子
的张后主、李后主们认为这些电影不过是西方的形象诡计:冷战后的
西方“只好在电影中将中国变为那个昔日的驯服的殖民化的他者了,
这会让西方的观众获得一种幻想的满足”、“陈凯歌、张艺谋这类导
演则又一次创造了一个西方话语支配下的新的第三世界电影的类型,
它为西方再度提供一次欲望的满足。”(引自张颐武《寻觅旧上海:
后殖民时代的神话》见《电影新作》1995年5 期)。我有点听烦了,
除了模仿杰姆逊那极左狂热的呼喊与细语和塞义德那受虐之后的娘娘
腔惊声尖就不会唱点别的调子。
正如我在上文指出,这些影片是我们在造自己的梦,是我们在找
自己,并不是西方人钻到陈凯歌、张艺谋脑袋里来找我们。如果说
哪地方跟别人的风景有点象,那也是我们借张、陈的眼和手在画世人
都爱看的图景。把张艺谋、陈凯歌和我们这里的思想者当作终极标靶
是取得左派教授话语卖办营业执照的最便捷途径。这张执照是两面可
用的:既能在本土顶着民族主义的桂冠登堂入室,进入社会的高层庙
堂和学术的教室,又可凭借话语暴力打进西方话语的游戏场,让别人
听到自己鹦鹉学舌的中国回声。
可怕的是他们对法国1968年风暴和中国文革的天壤之别视而不见
或胡乱解释。在中国,思想面对的不是催泪弹。思想的成长需要游戏
规则,需要催泪弹。而后主们的话语对本土问题的热情不足、对具体
的本土艺术品相关性太小,只骂八国联军,不谈雍正皇帝。
在我看来,怀旧作品的底层是今天中国大众心底那滚动不息、本
无定向的湍流在奔涌,这是中国百姓的梦和心底欲望在惊涛拍岸。
也许,这只是潮打空城?这是我们今天在塑造新个体,这是我们
在找寻新的富裕路——在商业伦理的氛围中,走规则竟争的致富路。
这些电影首先是给中国百姓看的,被很多评论家狠狠训斥的《摇
啊摇,摇到外婆桥》完全是上影厂投资、国内票房成绩很不错。
这是我们在找寻自己、塑造自己。我们不应随便打碎自己的梦,
不要随意阉割梦中的自己。
|
【声明】榕树下每周精选的所有文章,版权属作者个人所有, 感谢“榕树下”授权,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
